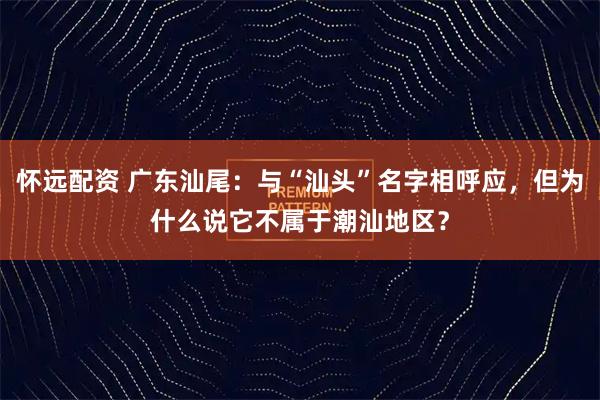
在这个时代,城市的名字像风筝的线,被人们拽来拽去,最后落在谁的手里,便认定了谁的身份。于是便有潮汕、粤语、客家、广府的争执与自豪,像尘世间的许多划分,总在说不清楚的地方留下一点模糊。此处,便是刘小顺的旅行与生活研究所所记。许多人把旅行写成脚程,而我更愿把它写成心的丈量。前些日子,我随一队房车,沿着汕尾的海岸线走了一遭,也在这段路上,看清了一个城市的边界与非边界。
汕尾,位处广东省的东南沿海,海风吹过的地方,总是带着历史的盐味。那天清晨,海水像一块被磨光的镜子,映出车队缓慢前行的影子。我第一次来到这里,对这座城市的熟悉感,像被海浪一遍遍拍碎的镜面:起初以为它与潮汕并肩而立,像两只彼此呼应的海鸟,名字听起来似乎同根同源。有人把它称作潮汕的一部分,有人则说它并不属于潮汕。此情此景,我的脑海里并不急于给出答案,只愿把问题抛给路上的每一个人——包括我自己。
展开剩余76%抵达后,我向当地的朋友报告说,我来到了潮汕的边缘,然而他们的回答却把这边界给抹平了。汕尾并不属于潮汕,这句话像一枚硬币落在我的掌心。严格意义上,潮汕地区通常指潮州、汕头、揭阳三城的组合;而汕尾,似乎在这套逻辑之外。于是我回想起往日听人说潮汕地区的边界,像一个简易的地图,被反复涂改、被新的叙述覆盖。为什么会如此?原因并不单一,历史的疤痕总是比今天的对话来得深。
有人说,历史曾经把汕尾划给惠州府管辖,虽有过短暂的被归入汕头的记录,但时间并不久,大家的记忆里仍把它排除在潮汕之外。也有人提到,汕尾的文化像海上的潮汐,潮汕、客家、广府等诸多水域在此汇聚,形成一种多元的海味。于是,一部分汕尾人自认是潮汕人,另一部分人则对潮汕的身份标签持保留态度,仿佛在海风中找不到稳固的岸。
与我同行的广州朋友更是吃惊:汕尾的粤语口音并不稀奇,反而让他们惊诧。在他们印象里,潮汕人多讲潮汕话,粤语并非主流;而汕尾这边,粤语讲得相当娴熟,仿佛把语言的边界也抚平了。于是,我在这座城市的街巷里,看见了语言的折射:历史的边界并非只有地名的标签,还有人们日常的口音、手势、习俗,乃至饭桌上的一口汤的温度。
汕尾的地理位置,像一块被风吹过的木板,东面靠近潮汕,西面则贴着珠三角的惠州与深圳。于是它的文化呈现出一种自我拼接的姿态,既有潮汕的脉络,也有粤语圈的呼吸,还有客家、广府等元素在此混酿。有人坚持若把视野拉宽一些,汕尾也应当纳入潮汕的范畴;但这种说法始终无法彻底盖住另一面:它有自己的独立性,有时甚至以一种不愿被定义的姿态存在。如此这般,汕尾成了一个关于身份的争论场,也是一个关于文化共生的案例。
我不打算给这座城市下一个简单的定论,而是愿意把它作为一次对“地区”与“认同”的观察。你来过汕尾吗?你对这座城市又有怎样的印象?你是否认同它属于潮汕的範畴,还是愿意把它视作一个独立的海港城,拥有自我的故事?这些问题并非寻常的地理标签所能回答,它们需要时间来辨识,需要人们在喧嚣之外静下来聆听海风的回声。
未来若还有机会再到广东旅行,我想继续走进汕尾,走进那些被海风轻拂、被历史打磨的角落,听一听普通人对身份的看法,看看城市如何在自我定位与他者认知之间找寻平衡。欢迎大家把你们的观点写下来,与我一同思考这座城市在你心中的位置。
更多的记录与思考,请关注我:刘小顺。愿这海上的日子,带给你我更多清醒的视角,与对世界更深的善意。愿每一个对未知抱有好奇的人,都能在风起时保持一颗勇敢的心,在潮汕与粤域之间,找到属于自己的岸。愿汕尾的海風吹散偏见,吹来理解与温暖;愿我们在看待世界的路上,始终怀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,向着光明与希望前行。
发布于:山西省金富宝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